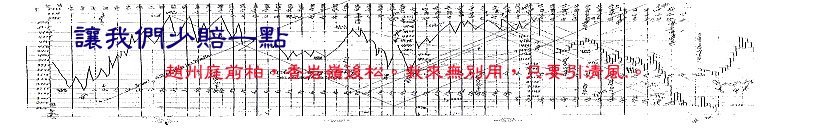這一次的除夕地震讓我想起了很多往事。讓我們先為往生者默哀。
越是混亂的地方,油水就越多。就會出現一些想要從裡面淘油水的人,我一直思考,這是我們人內在精神負荷外在這個肉體沉重的負擔所下的選擇。
九二一時,山上的屍骨未寒,山下已經有計程車招覽生意上山觀光。更有甚之,兩派計程車還為了拉生意打了起來。山上還屍骨未寒…
這就是人性。而人性源自於肉體的沉重。
想當初,個人有幸(其實是黑到底了)在SARS時期在軍中參與了重要的SARS病患收容任務。部隊找了個未完成的新營區,就開始規畫如何收容SARS人員。我,黃排,高醫官,和陳班就被指定到這個營區駐守。營區的人告訴我,你完蛋了,真得黑到家了,要退伍了還碰到這種任務。你會被傳染的,死亡率很高…。一堆恐怖言語飛天。但對一個老鳥來說,以部隊的風紀,演演戲可以,真要幹,是不太有力氣的。以高醫官的說法,連外面的醫院都搞不定的東西,就憑部隊幾個醫官想搞定。少開玩笑了。
出發那一早,就看到黃排忙來忙去,不知在幹麼。
喂,黃排,你在幹麼,要出發了。
去去去,不要吵。
看他不耐的樣子我就在車裡等著,不久,看他匆匆忙忙上車,手裡提了一袋白白的東西。我就問他這什麼。
他就說,快出發,不要問啦。
到了新營區他看著司機離開,就拿出了五件防護衣。三件放在臨時辨公的桌下櫃。另兩件就叫陳班藏在他的櫃子裡。
我說,黃排你當真了。
黃排說,這事非同小可。他當兵的老爸打電話緊告他了。
我想對哦!他們是軍人世家,會有一些消息,但我心裡還是想,部隊這個風紀能幹什麼?
這樣安然的過了十數天,一點動靜也沒有。對面則慢慢的蓋起來一個小辨公廳,一隊憲兵隊就這樣駐守進來,黃排一早就過去打個招呼,好像是要雙方不要為難彼此。出去前,嘴裡叨了一句,媽的!我還以為這些長官都不敢碰這裡。下午四點半,我照著每天例行公事,上大樓查看房間。然後上頂樓陽台打一趟太極,不久就看到憲兵隊五點開始的下午三千慢跑。我看著,心想,在一個沒有長官看著的地方,這種自我紀律可以多久。就一個星期。
現在變成,我打完太極,就蹲在我們這邊的辨公區外抽根煙,對面不再跑步的憲兵下午變成打PS,放鬆的時間,他們的士官長,也走出來抽煙。看到他走出來,我總是半開玩笑的站起來跟他敬禮,他總是用拿煙的那隻手揮一揮。有一天,他走了過來,問我有沒有煙。那時的習慣身上都帶著二包煙,我把新的煙拿出來,往手上敲一毃,眾所周知的,白長!一定要打一打,菸才會實。士官長一看,你什麼年紀,現在還有人抽白長。我跟他說抽來抽去還是這個好抽。他抽了兩根。突然門口快速的停了兩輛小青蛙,我一看,用力的彈開手上的煙,嘴裡不自覺的叫了出來,媽的,指揮官。整包煙掉在地上,趕過去按下電動鐵門的按鈕。馬上又跑到辨公區拿自己的小帽,大叫一聲,指揮官來了。
當我又衝到大門,大喊,指揮官好。眼裡還撇著辨公區,看到他們在裡面著裝。快啊!快啊!穿個衣服這麼慢…我心裡一直念著。指揮官下了車,終於看到黃排跟醫官走了出來。我對著指揮官說,黃排跟醫官在那裡,請跟我來。後面這時已經停了四五台記者車,一堆記者開始拍照。換黃排他們接手,我慢慢離開,看著指揮官那仰角四十五度的下巴。讓我一直覺得他好像有穿披風的樣子。我回到辨公區,看到支援的化學兵穿著化學裝,背著裝滿水的消毒罐,開始噴每一輛車的輪子,我就走到了憲兵那一邊去。士官長看著我走過去,把剛剛的煙拿給我,指著化學兵說,以演技來說,這化學兵演的不錯。我當場有一種不知哭笑之感。突然有一個陌生人靠了過來,請問一下,負責的長官在哪裡?我就說都在大樓那裡,請問你是?我怎麼覺得這個人很面熟,心情稍為有點恢復,這不是小蜜蜂的老闆嗎?啊!你是小蜜蜂老闆!對方說,對啊!我是來裝自動販賣機的,因為你們接下來就有病患要來了,他們會想要喝飲料。我說,哦!那你等等好了,他們都在忙。
經過半天的折騰,黃排走了過來,還沒來得及跟我說話,小蜜蜂老闆就靠過去了,我是來裝自動販賣機的…。我看黃排耐著性子聽完,就說,你下個星期再來,我問問我們營長。又拗了半天,老闆才走。黃排靠過來,說,媽的,不要再讓奇奇怪怪的人進來,病患真的要來了。
接下來,好像消息走漏了,隔天早上,營長自己來視查我們這裡的狀況,我在外面打掃,看著營長在辨公室走動,黃排跟著記錄缺失。不到十分鐘營長就離開了。營長臨走時,我過去車旁站著,照例,黃排要喊敬禮,我就一直等著,嚨…車開走了。我推了一下黃排,怎麼沒喊敬禮。黃排擠了我一下,走到辨公室裡,喊個屁,你沒看他把防護衣帶走了嗎?我心想,就為了防護衣啊!大老遠跑這一趟,就為了拿防護衣,營內不是很多嗎?一句經典的話語,浮上心頭,別人的孩子死不完。
下午,不知道那裡來的阿婆,居然從大樓走出來。我過去問,阿婆你怎麼進來的?阿婆連理都不理我。黃排看了,就問我,他怎麼進來的?我說,我也不知道。黃排說,那你去問清楚。我回頭一看,阿婆突然就消失了。晚上吃飯,我就跟陳班講這事,陳班說,她就住隔壁,從我們來這裡就天天都看得到她在營區裡,你們是第一次看到嗎?高醫官就說,那他怎麼進來的,你們去問清楚,不然到時SARS病患偷跑出去看你們怎麼辨?我想高醫官這口氣是怎了,最近他越來越奇怪了。
隔天一早,我就跟陳班去問阿婆怎麼進到營區,高醫官也跟來。我實在有點忍不住,就問,醫官,你這幾天情緒怎麼不太穩。高醫官嘀咕嘀咕的。下午我先跟陳班去找阿婆說的牆洞。突然跟在後面的醫官就大聲的說了,我跟你們說,現在外面疫情變的很可怕了。非常可怕,我同學都說只要碰到很可能會死,已經有醫生出事了。如果病患進來,我們一定會陪葬的。我停下腳步跟醫官說,相信我,病患不會來。這只是一個秀。軍隊就這個能耐了。
看完牆洞,回到營區大門,看到一個人探頭探腦,後面一輛車上面載著四台販賣機。我走過去,老闆,你又來了。老闆問,你們長官在嗎?我來看看能不能裝機器。陳班說,我們去問問。我心裡覺得有一種罷王硬上的感覺。
隨便他,隨便他,讓他自己裝,你們不要理他。黃排還在氣營長拿防護衣的事。你們阿婆問好了沒?我說,後面山坡那一段牆有一個洞,我們再把他補起來就好。下午,我跟陳班找了一些癈木料要釘,化學兵學弟就跑過來說,衛生局的人來視導,說要看我們準備的狀況,後面又是一堆的記者。我跟陳班放下東西跑到前面協助,看到記者圍著憲兵辨公區,我過去看了一下,哇靠!怎麼在跟大樓裡面的人視訊。靠…這士官長是什麼時候搞這一套東西出來的。看著士官長在大樓裡透過視訊叫著他的憲兵排,心裡有一種感覺越來越強,說不上來。
吃晚飯時,高醫官又在嘀咕著,真得會來,到時大家要做要準備,非常危險,尤其你,你要退伍了,老兵八字輕,一定要小心。這飯真得變很難吃,氣氛真差。吃完晚飯,陳班叫了我一下,我們抽了根煙,陳班說,他身上還有500元,問我剩多少,我說還有一百多吧!他提議,我們去買個啤酒讓大家放鬆放鬆,我說好,就過去跟憲兵士官長說一聲,告知他等等會出去買個東西。順便酸一下士官長,你們下午的視訊還真屌,你的演技很不錯。士官長重重的踢了一下我的屁股說,小兔仔子,我年紀不小了…沒大沒小…
我嘻嘻哈哈的跑了。
十點多,我跟陳班跑遍了附近,連平常常去的有露出潔白大腿的檳榔西施的檳榔攤也沒開,蕭條一片,只剩下遠遠一家PUB,我們進去問了一下啤酒價錢,陳班用肩推了推我,我往他推的方向看去,一個低胸辣妹正在吸著長島冰茶。人家說當兵二三年,母豬賽貂蟬。
我回過頭去看著老闆問,一杯長島冰茶多少。
老闆說:三百。
陳班就說,那兩杯帶走!
我們偷偷的從沒有補好的牆洞回到營內,坐在要補牆洞的木板上,看著天空,繁星點點,旁邊幾座墳墓,寧靜的待著,黑暗中像幾隻大熊。我慢慢的喝著長島冰茶,讓醉意慢慢襲來,一種舒暢充満全身,微風徐徐,心裡早就忘記要買啤酒給大家這事。一點點罪惡感,一點點浪漫,最後在扶著陳班回辨公區時,看著陳班吐了一地。這是當兵的日子讓我印象最深也最美的一晚。
一早,黃排把我推醒,醫官呢?
我就說,沒看到,可能在運動吧!
黃排大叫了起來,媽的給我跑了,他連衣櫃東西都不見了。趕快把人找出來。
我心想,天啊!這是逃兵。
陳班摸著頭,可能還宿醉著,說,他居然跑了,這個貪生怕死的傢伙。
我跟陳班到大樓一間一間的查看,廁所一間一間的找。還發現了有人在裡面大便沒給我沖水。
後來戰情官打電話來,說醫官回營區了,我跟黃排馬上開車要去接他回來,到營區時是中午了,大家都在用餐,好不容易找到醫官。醫官說,營長調他去支援屏東一個單位下基地。等一下就出車了。我想,醫官你苦了。
幾個學弟來問,我們要不要用餐,順便話家常,我叫了營部的學弟過來,要了兩件沒帳的防護衣,拿給黃排,就一起上車走了。我跟黃排說,沒帳的,就送你了,不過跟你說,用不到的。
自此過了一個月,不再有任何人來過這個營區,一直到憲兵隊徹了,我也退伍了,自始自終,沒有一個病患來這裡。
之後,心裡面的感覺隨著日子越來越明,我想問,各位參與做秀的人員,你們都得到自己心裡想要的東西了嗎?